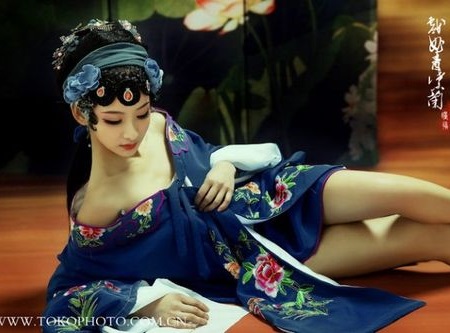其传奇今存《西湖扇》、《化人游》、《蚺蛇胆》、《赤松游》四种,“沈雄清丽,兼而有之”,尤其《蚺蛇胆》一剧,“结构谨严,关目生动,词藻尤清丽遒健,远胜《鸣凤记》之拉杂散漫。”[7]
然由于当时触犯时忌,使上官不敢进呈,今也有种种原因,丁耀亢之传奇未为曲家所重,殊为可叹!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9.html
小说《续金瓶梅》,今可考定为丁耀亢在顺治十八年(1662)六十三岁时所作。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9.html
这是因为此书卷首《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子解序》称:“今见圣天子钦颁《感应篇》,自制御序,谕戒臣工。……亢不敏,卧病西湖,……以不解解之。”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9.html
西湖钓史《续金瓶梅集序》也说:“遵今上圣明颁行《太上感应篇》,以《(续)金瓶梅》为之注脚。”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9.html
可见此书创作离“天子钦颁《感应篇》”不远,而作者当在杭州之时。今查,清顺治十三年上谕刊行《感应篇》。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9.html
时丁耀亢在直隶容城,后至福建惠安,至顺治十七年六十二岁时告退,其间不可能创作《续金瓶梅》。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9.html
翻至小说第六十二回,作者根据《搜神后记》中丁令威的故事和自己切身遭际,虚构改编成一个三次转世的故事: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9.html
东汉辽东鹤野县仙人丁令威,五百年后为临安西湖匠人丁野鹤,至明末又有同名同姓的一个丁野鹤,自称紫阳道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9.html
这段故事不但较为露骨地寄寓了作者的民族情绪,而且为研究作者本身提供了信息。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9.html
鲁迅先生首先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据此解开了作者之谜,指出紫阳道人即是丁耀亢,此书当成于清初,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就在这里,鲁迅先生忽略了这样一段话: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9.html
……临安西湖有一匠人,善于锻铁,自称丁野鹤,弃家修行,至六十三岁,向吴山顶上结一草庵,自称紫阳道人。……留诗曰:“懒散六十三,妙用无人识。顺逆两相忘,虚空镇常寂。”
这显然是夫子自道,点明了此书即作于六十三岁之时。揆之丁耀亢的一生经历,也正相符合。
此书即于当年开雕,世称有顺治原刊本者当为此本。然此书一出,祸即天降。
康熙四年乙巳(1665)八月,六十七岁的丁耀亢即以此书下狱。其《归山草》有诗记其事。诗名较长,曰:《乙巳八月以续书被逮,待罪候旨,至季冬蒙赦得放还山,共计一百二十日。狱司檀子文馨,燕京名士也,耳予名,如故交,率诸吏典各醵酒,三日一集,或至夜半,酣歌达旦,不知身在笼中也。各索诗纪事,予眼昏作粗笔各分去,寄诗志感》。诗曰:
独坐怜寒夜,圜墙起鼓声。雪晴光不定,月暗影空明。椽史藏文士,穷交仗友生。莫轻谈往事,一醉颂升平。
后又有《焚书》一首:
帝命焚书未可存,堂前一炬代招魂。心花已化成焦土,口债全消净业根。奇字恐招山鬼哭,劫灰不灭圣王恩。人间腹笥多藏草,隔代安知悔立言。
这些在铁幕下面迸发出来的沉痛诗句,隐约地透露了这部书的得祸之由并不在于“诲淫”,而在于“轻谈往事”和欲为人间“立言”而已!
这和刘廷玑给《续金瓶梅》所加的罪名首先是“背谬妄语,颠倒失伦”,也相一致。
《金瓶梅续书三种》
另外如龚鼎孳《定山堂诗集》中的《赠丁野鹤》其三也透露这部续书遭焚的基本原由:
江山如此恨人留,痛哭书焚向古丘。热血空怜霜草碧,遗民今见竹林游。垂阳袅袅能愁客,彼黍离离又报秋。避世不如忘世逸,逍遥神解失金牛。
后来,康熙帝之所以还是将丁耀亢释放,恐怕由于他刚下诏表过这样的态:“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8]
然而,这一百二十日的铁窗生活和不得不将一部“奇字”付之一炬,对于一个望七老人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丁耀亢从此两眼昏然,丧明逃禅,自署木鸡道人。文人之厄,莫此为甚!而一部《续金瓶梅》,从此也就被打入地狱,难见天日!
现在,我们打开《续金瓶梅》,劈头就是一篇《太上感应篇》。
丁耀亢想把整部小说就当作《感应篇》的“无字解”,即不直接用一般的笺注诠解等方式来解释,而是别出心裁地用小说故事来加以“参解”。
丁耀亢之所以这样做,不能说他没有拿着皇上推荐的《感应篇》来作大旗打掩护的用意,然而应当说,主要还是由于生逢“天下无道”之时的他对于《感应篇》的欣赏。
《感应篇》一书的内容,多取自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以因果报应为纲,劝人为善遏恶。
正如丁耀亢在《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序》中所说:“天下有道,听治于人;天下无道,听治于神。”
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那混乱的年代里,还有什么比用因果报应更有效力地去鼓动人们为善呢?因此,《感应篇》自《宋史·艺文志》始有著录以来,一直非常流行。
特别是明末清初的许多小说,不但往往以因果报应、劝善惩恶作为其创作的主旨,而且常常直接描写和引用了《感应篇》以及《文昌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等“善书”。
如《西湖二集》卷三《马神仙骑龙升天》就有马自然引用《感应篇》劝人的场面,《红楼梦》第七十三回也写到了迎春读此书[9]。
丁耀亢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难免也受到了影响。今从其卷首所列引用的书目来看,尽管有三教九流五十四种,但《感应篇》无疑是贯穿全书、引用最多的一种。
他所引用的《感应篇》的语句大都在每回的开头,作为故事开展的依据。而在这些语句中,除了“三台北斗神君”一段宣扬迷信和报应纯属糟粕外,其余多为劝人在道德上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