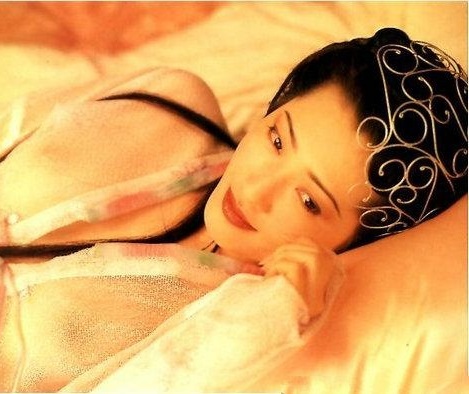三是处在当时文以负载更多政治功能的文强诗弱的总体格局,诗文异体论的提出,意在抬高诗歌的创作地位,赋予其以相对独立的审美空间。
具体到李东阳对诗“体”的阐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从“兼比兴”、“协音律”[13]的角度,探讨诗歌的文体性质及其艺术属性,包括诗歌基本的修辞艺术以及诗合于乐的原初特性,分辨诗之为诗的文体的独特性。
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他较有个性的诗学立场以及台阁诗学趋于分化的某种迹象。若从考察成、弘之际台阁诗学的整体格局出发,我们还可注意其他馆阁文士所持的诗学立场。
总体而言,此际的台阁诗学作为有着官方背景的文学系统,其维护正统、尊尚教化的实用意识仍凸显在馆阁诸士的诗学观念中,成为台阁诗学主导话语的一种延续,体现了它的强势的影响力。
但同时,不同程度淡化诗歌的实用色彩,重以艺术审美相鉴察,亦从一些馆阁文士的论诗主张中传递出来。
如吴宽、王鏊等分别强调诗家自我心志的塑造,倾向诗歌艺术韵趣的营构,注重诗心与诗趣的独特表现,自和实用色彩浓厚的台阁诗学的主导话语不可等而观之,在维系传统的同时又融合了某些变化。
假如从包括诗学思想在内的明代文学思想整体发展格局观之,或认为“整个明代文学批评的方向受到前后七子的重大影响”[14]。
此说并不过分。明孝宗弘治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倡兴诗文复古,成为明代中期文学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的突出表征,而前七子所构建的复古诗学,也成为明代诗学思想史极为重要的一环。观李、何诸子复古诗学的基本宗旨和审美取向,如一言以蔽之,则可说是“反古俗而变流靡”[15]。
总体上,诸子对于古典诗歌系统的辨察,大多表现出追溯本源的倾向性,他们将《诗经》、汉魏古诗、唐代尤其是盛唐近体诗列为重点宗尚目标,旨在追溯古诗和近体诗系统的本源。这还不只是时间上纵向上溯的一个概念,更主要的是,诸子将古诗、近体诗的形成和完熟的源头,与它们各自原始的审美特征联系起来加以审视,赋予这种原始的审美特征以足供取法的典范意义,以返至他们所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古俗”,并且认为,自此出发,才能切实把握古典诗歌系统之正脉,维护诗道延续发展的纯正性。
鉴乎此,他们更用心去体认、推尚古诗和近体诗的原始的审美特征,注意分辨古典诗歌历史进程中的近“古”与远“古”的承传及变异之现象,突出了古典诗歌系统审美之原始性与典范性之间的对应关系。
特别是针对诗歌体制展开多重释说,成为李、何诸子复古诗学的中心议题。
通观李梦阳、何景明对于诗歌的定义,其反复述说主情为诗之所本这个看似简单而又重要的传统命题。
无论是李梦阳提出“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批评“宋人主理作理语”,以为“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16]?从诗主情而非主理的定性,引出诗文的分界问题,还是何景明有言“夫诗之道,尚情而有爱;文之道,尚事而有理”[17],以“尚情”与“尚事”区分诗文不同的撰作取向,都成为诗本主情命题的逻辑基础。
比照“诗言志”、“诗缘情”这些诗学的传统命题,李、何申述诗以主情为本,虽不能算作革新性的倡论,但因其主要基于对诗歌史的检察,基于诗歌实践和诗学传统命题形成的冲突,仍体现了富含警戒和纠正意味的特别价值。
在他们看来,特别是“宋人主理作理语”诗风的兴起,对诗歌的抒情体制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淡化了诗歌作为抒情文体的纯粹性,甚至模糊了诗文各自既定的界限,扮演了反诗歌抒情传统的角色。
如此,他们反复明确关乎诗歌本质的抒情体制,排斥宋人的“主理”诗风,诚然含有审视诗歌发展历史、为诗歌抒情传统进行正本清源的自觉意识。
不仅如此,关于诗歌体制的问题,李、何等人又分别提出过格调说。尽管此说不能代表李、何等人论诗主张的全部,他们也未曾以格调来总括自己的诗学立场,但说李、何等人论诗重视格调又确是事实。
李、何论格调,对其意义的辨识多具特定的指向。如“格”,重点指向的是不同作品共通与本质的品性,这种共通与本质的品性又蕴含在作品之“体”中。
因此“格”、“体”之间关系紧密,判别作品是否合“格”,主要以古作特定的体式或体格为衡量基准,这也是“格古”或“高古”之“格”铸成的必由途径。
如“调”,既被注入了诗人情感性气的质素,不能完全外于诗人“性情”而求之;又其基本意义和判别标准,被定格在诗歌的音响声调上。
李、何主张的格调,虽各自的意义界限或有交叠,未能完全分立,但仍具有相对明确的限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源自他们对于诗歌体制认知的细化和深化。
《王世贞研究》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8.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8.html
注释: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8.html
[①]《诗薮·续编》卷一《国朝上·洪永、成弘》,第3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8.html
[②](美)刘若愚著、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第1页至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③]参见(英)阿拉斯泰尔·福勒著、杨建国译《文学的类别:文类和模态理论导论》,第1页,第256页至30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8.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8.html